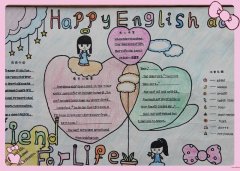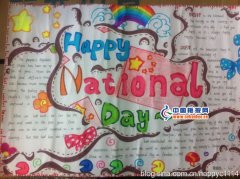我怀念的
编辑:高中作文网我怀念的
我怀念的九(13)班 胡筱娅
我总觉得还在那里。
抬头看四楼的时候,辅导室的灯就好像还亮着,晃动着二月四号前那二十多天。
如果推开门,面前会是那个长长的走廊,再往前走就可以接到水。
如果推进门,眼前会是四十张陌生又熟悉的脸孔,埋头题海里。
我心里潜意识地念叨着,只要走过这四层楼梯就是教室——到门口了。毫不经意地打开门,就像是往常那样极为习惯性细小的动作。
心口一窒,很空。桌子是齐的,如群蚁排衙,划分好的一排排一列列,凳子一张张倒扣着,像棋盘开局前置好的棋子,可是上一轮结果早已知晓了,这已经是重新开始的一轮了吧。
所有的棋子是不是应该再次到位重新来过一遍呢?
没有的。这一切都只是输掉了棋的事情,就像是输棋的人,总是不愿意相信自己输掉的事实。一切都仅仅,一个结果。人们总说,过程才是最重要的,可你能说结果不重要吗?一字之间,相隔了十万八千里也望不到边的感情。尽管早早地心知肚明了差距悬殊,清楚这二十天也只是杯水车薪,但最后得知结果后还是会木然地愣在原地,挂着苍白的笑容说着鬼话:“其实我早就知道了。”
但仅仅单一的二十天里我记住了这个可爱的教室。仅仅压抑的辅导室让我记住了这个可爱的二十天。“领略过海风滋味的人,永远都忘不了这种滋养。”虽最终无果,但对我而言,是不会后悔的二十天。
那段时间的记忆不深,脑海浮现的只是千第1篇律但每天又有一点点的新鲜。如朱钊楷上语文课时,他若无若有,似真亦幻的回答答案,大冬天的肩披秋季外套,“马作的卢飞快”,颇有不羁少年闯荡天下之感;小花时不时魔音绕耳,两颊揩擦着粉红,在与那四个来自不同班级的女同学的对比下,像来自两个不同的世界,她们仅仅只是一个眼神,偶尔来个小小的一瞥;又或是每天中午特定时间里陈行健妈妈的那一句门缝间的微弱呼唤:“行健......”;还有王奕嘉的日常活跃,挑动着眉毛,矗着那油亮亮的眼睛,用犀利的语言和独具一格的想象,一语道破天机,说完还颇为自我欣赏的啧啧称赞,迎受着来自全班人以他为圆心投射而来的目光。等等等等。
一切由淡淡的悲伤和淡淡的快乐组成,在小小期待,偶尔的兴奋和沉默的失望中度过每一天,然后带着一种想说却说不出的明白。在过程中释然。
因为每件事格外细小,微弱到转瞬即逝,迅速到不可挽留,可偏偏那被你捕捉到的细节,怎么都挥之不去。于是就连郑老师的日常巡逻也成了那段时间里,平复濒临战场严阵以待而心慌意乱的灵丹妙药。作为一个女生,既怕那一段时间老师来找你谈成绩那些事,又矛盾地担心老师不来找你谈话,那一种失了习惯性的注视后的极不习惯。
郑老师是个很能“画饼”的人,当然他也是会寻找时间的,尤其是在教室里人较为稀疏的饭点,同学们三三两两地扩散游动着。在这时候你极其容易便能荣升会成为主任的画饼对象。郑老师的背窄而长,肩是鞠着的,他便这么像龙头拐杖似的走向你,嘴角悬挂着主任独树一帜的特质微笑,眉毛和嘴角拧动成气旋,长手一捞,伴随着椅子抽出与地面的摩擦声,他的背掰成如满月的雕弓。画饼前,他会先试探性伸长脖颈,然后开始一大连串的关于最近的学习状况的提问,尽管答复总是差强人意,郑老师还是会用宽大的手掌拍拍你的肩,笑着给你画出一个“要自信”的大馅儿饼:“没事,可以的。这个问题解决了就好了。” 于是,你捧着这馅饼总算聊以自慰了这仅剩十多天焦灼,皲手茧足着向那个二月四进发,像加了料的鸡汤,热滚滚地翻腾着热气,在你的心里连续冒泡。
“我一点也不紧张,”郑老师在提招前说,“我每天晚上还都睡得很安心。”我对这话印象尤其深。他表示自己带过这么多届学生早已惯看秋月春风,而且不断强调,我们的考上提前招与考不上,对于学校而言,只是个数字上的变化,而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生的转折点:“重视点啊你们。”
“我一点也不紧张。”
我不知这是郑老师作为一个班的支点故意这么讲来安慰我们的,还是在安慰他自己。
谁不知道,他常埋在墙角那“挑战自我”的四个字下看那一张张罗列的成绩排名,在白纸黑字的姓名里圈点钩画着那张“生死薄”。那一刻的郑老师是极为严肃的,执行这每天必不可少的庄严仪式。他一手捞开排名上的白纸,另一手拿着红笔和目光成射线不断向下扫视,而有时又用食指跟着口型不断清点人员。单科科目分数里画圈的是偏科的;画三角符号的是要留意观察的;姓名前的一列数字是用来排序的;还有一条细长的大红杠夹在某两个紧挨的名字间,作为上与不上提招的分界线。不过,等开学回来时,那几张成绩单已经被撕掉了。
还记得流感肆无忌惮席卷我校时,尽管我们早已听得双耳生茧,郑老师还是不断叨着。于是,“呕吐物”这个新名词,仿佛开始变得比一切事物都更加可畏,它不让你一命呜呼,却让你像是推进了泥潭里,任由朝夕相处的小伙伴们远走高飞。而自己,就算集万千技能于一身也无济于事。
就在提招前的某天,呕吐物惊现实验楼四楼。
想想不安心 。
上数学课时,郑老师慌张地推开教室门:“四楼男厕有一滩呕吐物,不知道谁吐的,你们待会别去四楼上厕所”。他不知还想说什么,却又咽了下去。
想想还是不安心。
郑老师打算合上门的动作还没做完,他又把上身往教室探进了一点。像是窥伺着什么动静。静默了一秒,四十个同学的视线停留在他身上,数学老师的拿着粉笔的手凝结在半空里。好像没什么不对的。吱呀一声,他关上了门。
紧接关门不到一分钟,哐当一声郑老师又火急火燎地来了。不过这次是窗户。
这回是不用想也不能安心了。
班里某同学因在厕所发现了呕吐物,经过流言的渲染,传到郑老师耳中,他便成为了呕吐物的制造者。打开的半张窗格刚好地框着他的那张脸——那张再熟悉不过的脸。它总在教室里人声嘈杂的时候,猝不及防得幽幽冒出,在一墙之隔的办公室和教室的窗户间,凝视。我记不清后来发生了什么,只是脑海不停地飘忽着他那因听不清声音而错综复杂的眉头。
到最后,我们班所有人都幸免了这一场飓风般的流感。郑老师笑着说:“我们实验楼这一排真是个风水宝地,我们一定会考得很好。”朦胧中,像是缺了一笔的画龙点睛。
“唉......”仿佛听到了郑老师的一声长叹,寂寂的一刹那,声音被拉长,诱出只留下一团模糊的背影:他立在办公室的窗边不知在望着什么,他的背是驼惯了的,身高让他无法也无需挺得再高点。他的手应该握着点什么,可是没有相机。
他很久没拍照片了。
有人说,文章为了什么事什么人写的,很重要。
我想是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