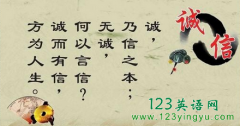我的父亲(2)
编辑:admin
后来,大姐的画似乎是不再绘了,家里却是多了一个怪异的事情——每到河里的水融冰,燕子翩翩归来的时候,隔壁邻居来到家里的次数就随着天气的温暖逐渐的增多——十分讽刺的是,他们来我家不是为了别的,正是为了求父亲制作风筝。那风筝上绘制的鸟儿岂是一个栩栩如生了得——有人让他画上几幅年画,那画中的老虎几乎吓得我哭出声音来;有人要他写上几幅字,那字好比有情感一般顺着我看不懂的轨迹飞舞叠加。小小的我,总是看着看着就那么醉了。
我总是一边看着大姐,一边看着来来往往的要父亲帮忙,却从没有买过一个毛笔,一瓶墨水的邻居。偷偷地追问着大姐:“为什么父亲自私的只允许自己作画、写字,却不让你偷偷摸摸的画上一只小鸟呢?”——好像,大姐是画了一只雄鹰,那雄鹰身姿矫健翅膀有力,就连那眼睛也好比真的雄鹰一样看着你。大姐悄悄地把它压在枕头底下,却被父亲看见了。他愤怒的拿着农民使用的铁锨,对着大姐的脸作势要拍打下去,并恶狠狠地对着抽噎的大姐追问着:“你要活,还是要画这些没用的东西?”
我看着大姐,心里真的想搬开铁锨说上几句顶撞的话,“为什么人家父亲那么好,就你这样不爱我们。自私的就知道自己作画、写字、高兴了还即兴作上一曲吹响你那清脆的墨笛,偏偏就不兴大姐作画。何况大姐这么小的年纪,就画的和你一般的好。”
奇怪的是,大姐竟然真的彻底的告别了绘画,做起了正常的初中生该做的事情。只是我不知道,每逢盛夏,炎热干闷得晚上,父亲习惯性的拉起他的二胡,我们静静的仰躺在场子边上,看漫天的星辰闪烁不止的时候,那低沉的音乐,如泣似诉的哀怨是不是也是在为大姐的无辜在哀鸣。
我听不懂音乐背后的故事,只是觉得这声音太悲怯了,不是很喜欢。可是,周围的邻居却是一次次的为父亲的二胡鼓起掌来。
慢慢的,在星辰和二胡声里,我们偷偷地长大,原先对于父亲的一次次的不理解,让我怀着复杂的心情对待着这里的一切。我似乎是他的另一个翻版,和大姐一样喜欢上了他认为不可取的东西,只是我喜爱的却是习作。父亲却不似当初反对大姐一样反对,只是冷冷的问我:“你有人家城里人的那个资格吗,人家有钱聘请专门的老师培训,有钱游历四方可以采风,你呢?”
就为这,我和他处于了阶级斗争的阶段,就像是两个完全敌对相克的水与火。每当看见大姐不在有半点怨言的劝解我,我总是嘀咕着:如果当初不是他逼迫你放弃,兴许你就是一个了不起的画家。
此时,心里对于当初二姐的争辩早已经信服入心里:这样一个小时候不在家里带我们,让我们几个孩子自己带自己,长大了处处打压我们的人,怎么会是那个模糊印象里哄唱自己睡觉的人呢?
“如果不是你自己带头总是喜欢写写画画,大姐会喜欢绘画,三姐会喜欢唱歌,我会喜欢写些东西吗?这所有的根源,还不是你日夜不变的二胡,日夜不曾停歇过的《二泉映月》?那曲调就连咱家的狗,估计都可以汪汪叫出来。”每每被你打击,我的心就愤怒的叫嚣着。那不可理解、无法宣泄的痛苦让我越来越疏远你,躲避你。
谁知道,你还是那样的严厉,严厉的让人害怕,让人深入骨子里的反感。我,成了家里面所有不敢与你对立的人当中,唯一一个敢和您唱反调的人。
不顾您一次次的书信,不顾您一次次的劝说下的狠话,故我的走,故我的做。
父亲的角色彻底的失去了他该有的存在,我不知道您是怎样的爱与恨着,我只是知道自己那么的渴望被包围,却一次次的被您打击着。直到有一天我扬着脑袋问外婆:我是他们生的么?
外婆诧异的看着我,“你不知道吗,你们家就你一个人最不让人省心,你爸为你操碎了心,你还不知道哈?你说。你不是他们生的,那是谁生的?”
是么?父亲,多么遥远的称呼。
“你爸爸他……在这个四界上,有什么东西是他不会的?你自己想想。可是,为了你们这些孩子,只能守在这穷地方。如果当初心再狠一点,或许就不是在这里过穷日子了。”外婆看着我,我想起那如水般看着母亲的温柔眼眸,那闭上眼睛摇头沉醉的拉着二胡的男子,那画着世外桃源三人对饮亭台小榭之间的父亲。
大姐说,父亲有着一颗诗一样的情怀,也有着强大的丰富无比的内心世界。可是,我怎么不觉得呢?他除了日复一日的每晚都拉二胡的习惯,除了矫情的画画花鸟,写上几个走神的字体,还会什么?每天都自私的自己去喜欢着诗词歌赋、吹拉弹奏,却不愿他的孩子们沾染上一点和文化有关的东西。
更不能让我所理解的却是母亲的态度,她一直跟在父亲身后反对着,只是因为父亲的反对。可是,我却清晰地记得,母亲曾经对我说过,她是喜欢父亲的二胡的。所以他日日夜夜的弹奏着他的二胡,母亲便会默默地坐在一旁聆听着。直到母亲病重,他的二胡声才戛然而止,此后夜深人静再不曾响起。
清楚的记得,母亲去世前一日,他一边扎着花圈、做着灵马,一边在我眼前第一次如婴儿般嘤嘤哭泣起来。我默默地站在一边看着他,复杂得反抱住自己,一颗心好比被饥饿无比得野兽在无情地撕咬着。